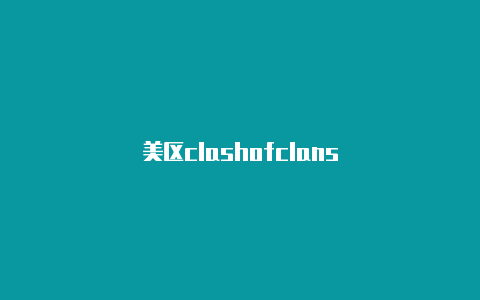
历史学走到今天,究竟是更细碎了?还是更宏大了?今日微信让我们跟随王晴佳、李隆国老师的新著一探究竟。
历史学出现的百家争鸣现状引起了一些史家的担忧。当今史学是否一如弗朗索瓦· 多斯所言,已经走向“碎片化”了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从肯定的一面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史学总趋势便是挑战近代史学的传统,力图走出其“宏大叙事”的架构,因而呈现出“碎片化”的现象。但这主要指的是西方史学的发展。荷兰历史思想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在《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一文中,曾经就此趋势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值得我们引用。他说近代以来的历史就像是一颗大树,有其“宏大叙事”作为躯干,史家的工作以论证、充实大树之躯干为主体,因为他们认为这颗大树代表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但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人们已经从研究大树的躯干转而研究其树枝和树叶,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这颗植根于西方文化的大树并不具有全球和普遍的意义。对此安克斯密特的解释是,西方史学已经进入了秋天,秋风萧瑟、落叶缤纷,让史家看到这颗大树背后的森林,也即西方历史的局部性。安克斯密特的比喻和解释,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迪皮希·查克拉巴蒂的名著《让欧洲区域化》的主旨相似,都指出了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必要。
由此,我们也可以对当今史学走向“碎片化”这一命题提出否定的意见,那就是所谓“史学的碎片化”clash98好打吗,主要指的是西方史学独霸天下的局面已经分崩离析,无法持续了。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正好为历史研究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藩篱提供了绝佳的时机。最近几十年全球史研究的兴起,便是史家挑战西方中心论,力图从新的角度考察历史变化的佳例。全球范围内史家对全球史的兴趣,自然与近年全球化的蓬勃开展有关。关于全球化的特征及其发生的原因,有关论述相当之多,此处由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有必要指出的是,全球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产物,但需要强调的是,史家从事宏观的历史考察,由来已久。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全球史有其前身,那就是世界史 (world history) 和普世史 (universal history; ecumenical history)。前者又分两种,一是以往史家对已知世界的描述,其历史十分悠久。如古代中国的司马迁、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西欧中世纪的奥托·弗莱辛和伊斯兰世界的塔巴里 (al-Tabari)、伊本·卡尔顿,都是比较有名的例子。二是近世以来建立在地理大发现基础上尝试写作的世界史,以18世纪英国史家集体写作的普世史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史家写作的世界史为典型,虽然后者对前者多有批评。前者的写作,基本上以史家自己生活的世界为中心,然后拓展出去描述周围的世界,因此比较注意划分自身与他者、文明与野蛮抑或“蛮夷”之分。而后者的眼界相对博大,希求用比较平等的态度展现世界各文明的进展,体现了一种“普世史”的立场。
19世纪中叶之后,兰克学派的兴起改变了前一个世纪的“普世史”传统。兰克强调民族—国家的兴起勾勒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主线,因此国别史成了历史著述的主要形式。兰克本人在晚年也想写作一部世界史,却未能完成。但从其架构来看,兰克的世界史是各个国别史的总合,与“普世史”的取径颇为不同。更重要的是,如果史家以民族—国家作为考察历史的基本视角,那么历史研究就无法避免西方中心论,因为民族—国家首先在西欧兴起,然后逐渐走向世界各地,成为现代世界政府构成的基本形式。
近代世界历史的这一走向似乎印证了兰克的观察,也即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将指引历史的前行。不过兰克没有预见到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不但充满竞争,而且常常剑拔弩张、冲突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便是一个显例。当代世界史家、全球史的先驱威廉·麦克尼尔 (William McNeill) 曾如此形容:“一次大战与自由主义历史观格格不入。19世纪史家颂扬的自由主义,变成了在敌对的战壕里选择生死的自由,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麦克尼尔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指的是英国近代史家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近代史》中所抱持的观点——阿克顿认为近代历史是进步的,其标志是自由在整个世界的不断扩张。但阿克顿像兰克一样,没能看到一次大战的爆发及其对西方文明的颠覆性影响。而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似乎更贴切地揭橥了当时欧洲人的心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演发成了一个近代历史学的危机。这一危机形成的关键原因在于,如果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发展是近代历史的主流,那么为什么这一趋向会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间相互残杀以及如此沉重的灾难呢?第一次世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都在寻求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建立国际调和组织,如国联 (League of Nations) 和以后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的成立等。这为世界史写作的重振,创造了生机。不过这一重振,仍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一次大战以后,逐渐开设和强化欧洲史和西方文明史的研究和教学,而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则要在1960年代以后才线年代席卷欧美世界的左翼思潮和,为史学界中世界史的兴起创造了一个契机。在西欧各国本来已有的对非西方文明的研究,得到了强化和深化,而在美国许多高校,则逐渐建立了“区域研究”(area studies) 的部门和单位,对西方世界之外的文明和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1982年美国成立了“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迄今已有三十五年了。这一学会的建立,正反映了当时区域研究的成果以及美国中学和大学对于世界史教学的需要。学会的人员构成,既包括大学教授,也有中小学教师。学会的几任会长中,也有不少是中学老师。可见对于世界史的兴趣,存在于各个层面,在教育界有广泛的需求,也反映出历史观的变迁广泛而深远。
1970和1980年代世界史的重振,为近年全球史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发展。或许我们可以用麦克尼尔的一系列著作来加以说明。麦克尼尔的成名作是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书。从他的书名便可看出,该书的写作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颇有关联。如所周知,斯宾格勒的著作对英国历史思想家阿诺德·汤因比 (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影响甚大。汤因比在战后的西方学界,声誉卓著,其名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卷帙浩繁、体大思精,是宏观考察、比较和检讨文明兴衰的重要著作。麦克尼尔一度崇拜汤因比,并与后者有过两年的密切接触clash98好打吗。但慢慢地麦克尼尔逐渐看出了汤因比体系的缺陷,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他的《西方的兴起》一书,虽然题目上似乎与斯宾格勒反其道而行之,但其实并不只是以颂扬西方文明为主旨。他在书中指出,自远古至大约1500年,中东地区是欧亚大陆文明的核心,其他如印度、中国和希腊都属于边缘文明。但在1000年与1500年之间,欧亚的农业文明遭遇游牧民族的沉重打击clash0.15版本,以蒙古征服欧亚大陆为高峰。1500年之后,没有受到蒙古人铁蹄践踏的“远西” (Far West,即西欧) 和日本等地区崛起,并以西欧为主力,形成了主宰世界的力量,重建了世界的秩序。麦克尼尔的这些观察,有他自己的创见。他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不同之处在于,他强调文明之间的互动和影响,不像后者那样孤立地考察文明的兴衰。而在冷战期间出版这本题为《西方的兴起》的著作,也有鼓舞西方人士气的作用,因此好评如潮。1964年,该书赢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麦克尼尔于1976年出版的《瘟疫与人类》(Plagues and Peoples),侧重点不同,但似乎更重视人类之间的联系,虽然他选择了以瘟疫的传播这样略显负面的角度来进行观察。不过,重视瘟疫的作用,必然会联系到人类生活的环境,因此此书也成为环境史的先驱作品。此后麦克尼尔继续努力,突出人类文明之间的互动。他最新的一本世界史著作是与他的儿子约翰·麦克尼尔 (John R. McNeill) 合作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The Human Web: 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从其书名便可看出,这是一部注重描述、分析人类各群体之间交流、联系的历史著作。更值得一提的是,麦克尼尔父子在此书中,竭力跳出西方中心的框架,不但重视16世纪以前中国等文明的地位和影响,还试图将西方兴起之后的近代历史,看作是与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的结果。
麦克尼尔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世界史、全球史写作的两个特点:一是强调文明之间的种种联系(冲突抑或互惠的交流等等);二是走出西方中心的框架,淡化近现代历史的重要性(西方的兴起是近代之后的现象,因此要走出西方中心必须走出美化、重视现代性的做法),从更广阔的视角考察人类历史的总体演变及其与自然环境乃至整个宇宙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特点的强化,也有助于促成从世界史到全球史的转变;前者是民族国家历史的总合,而后者则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视角,突出了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在麦克尼尔之外,较早提倡全球史观的是斯塔夫里阿诺斯 (L.S. Stavrianos),其主编的《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 of Man)初版于1962年,之后不断更新修订再版。斯塔夫里阿诺斯一直提倡一种全球史观,就如同从月亮上看地球,突出西方与非西方并没有差别,在文明发展上亦无分轩轾。近年来,杰里·本特利 (Jerry Bentley) 和赫伯特·齐格勒 (Herbert Ziegler) 所著的《新全球史》则更注重文明的多元传统和相互之间的碰撞与互动。该书的原名为《传统与碰撞》(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一主题,指出文明的多元性(因此用复数),是为了摆脱以西方文明、或某一个文明为中心的观点,而“碰撞”一词,则强调文明或地区之间的交流。以上两本全球史,都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史学,从“文明”(civilization)、“区域”(region)等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历史的演化和走向。它们不但在美国畅销,而且也被译成各种文字(譬如中文),在世界各地都有反响。以“文明”为单位考察历史的变化,也为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don) 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采用,成为当今学界考察世界局势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角度。
就全球史如何突破西方中心论,弱化西方崛起的近代意义而言,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在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和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是一本代表性的著作。此书的考察角度,与1970年代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Modern World System)一书和1998年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André Gunder Frank, 1929—2005) 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有可比之处,但取径和结论颇为不同。沃勒斯坦的论著,勾勒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与全球其他地区的联系,以“中心”和“边缘”的两极分化为主要思路,认为非西方地区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依附而存在。当然,沃勒斯坦对此现象持有批评的态度。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则淡化了西方兴起的历史意义,认为明清中国的商业经济已经在当时建立了一个世界体系。可是不管怎样,西方的兴起及其在全球的主宰地位仍然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象。彭慕兰的著作对此做了深入的探究,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看法。他认为在1750年以前,西欧和英国与中国江南相比,在经济发展上并无特色,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膨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受到了阻碍。但有幸的是,北美殖民地的开发使英国和西欧得以突破传统商品经济发展的瓶颈,继续长足发展,进而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以中国江南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分道扬镳。彭慕兰的研究,不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新的解释,而且他以江南而不是中国为单位与西欧做比较,也突破了民族国家视角的近代史学传统。《大分流》出版之后,彭慕兰声名鹊起,2014年转任芝加哥大学讲座教授,成为当今全球史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
总之clash98好打吗!,全球史的兴起标志了学界历史观、世界观的重要变迁。它借助全球化的动力(欧盟的成立及其欧洲各国边境的开放,即为一例),从一个在战后少人青睐的领域,一跃成为当今国际史学界的“显学”之一。2000年在奥斯陆召开的、有历史学界“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题,就是研讨全球化下的历史学变化。这一主题在2005年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再次得到重申和进一步的深化。上面提到的世界史学会,虽然成立于美国,但在近年却选择在世界各地召开年会(2011年的年会在北京召开,与首都师范大学协办,便是一例),其参加的人数也逐年增多。除了该学会在1990年出版的《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由杰里·本特利任主编直至他于2012年去世)以外,另一份《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也在2006年问世,2007年又有《新全球研究》(New Global Studies)的出版。2009年在纽约召开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主题是“让历史著述全球化”(Globalizing Historiography),由本特利等人拟定。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盖布瑞尔·斯皮格尔 (Gabrielle Spiegel) 做了相关的主题发言,号召史家重新检视经过后现代主义洗礼的历史阵地,让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产生更多的互动。
2014年美国当代著名史家林·亨特出版了《全球时代的历史学》,认可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走向,当代史家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写作历史。201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的《剑桥世界史》(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由梅里·威斯纳汉克斯 (Merry Wiesner-Hanks) 任总主编,本特利、彭慕兰等全球史的著名学者出任分卷主编。此书的编纂,其主要宗旨是取代阿克顿勋爵在19世纪末编写的《剑桥近代史》(The Cambrdge Modern History)及二战之后的《剑桥新近代史》(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后两本书从书名和内容来看,突出的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即西方如何领先世界以及非西方地区如何效仿西方而走向近代的过程。而《剑桥世界史》则与之迥然不同,其意图和架构都试图突破西方中心观和以民族国家为视角的传统,以区域 (regional)美区clashofclans、主题 (topical)和比较 (comparative)为取径,参以部分个案研究,作为全书的主要内容。
全球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史家逐渐对人类历史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的确,如果历史研究从注重民族国家等政治层面的内容转向比较区域和文明之间的差异,那么人类生活环境的不同及其影响便自然成了一个有益的视角。1972年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克劳斯比 (Alfred Crosby)写作了《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之后生物和文化的变化》(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 一书,描述了欧洲人发现美洲之后,人与自然环境如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美洲植物如番薯、玉米和土豆等如何促进欧亚人口的巨幅增长,以及欧亚传染病如何造成美洲人口的大幅减少等。1986年克劳斯比又出版了《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sim)一书,指出欧洲殖民主义之所以能够遍布全球,与欧亚大陆的植被、动物和疾病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其他地区的人类(亚洲在某种程度上算个例外)无法适应这些生态环境的变化。克劳斯比的观察角度,与杰瑞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 于1997年出版的名著《枪炮、细菌和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 十分类似。戴蒙德也指出,西方人主宰了现代世界,是因为欧亚大陆的环境相对“优越”,比如有比较容易驯服的马和狗等动物以及相对容易培植的粮食作物等,同时由于欧亚人经历了多次瘟疫产生了抗体,使得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比其他地区的原住民强了不少。这些由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人类之间的差异影响了世界历史的演变。
克劳斯比、戴蒙德等人的考察角度,显然已经不为政治层面的因素所限,而是扩大到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演化。这种“大历史”的取径,使得全球史与环境史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以上面提到的《剑桥世界史》而言,其架构和章节充分体现了史家希图在环境中描述、解释世界历史变化的努力。该书的第一卷讨论史前时代,自然环境与新石器时代人类迁徙之间的关系便自然成为一个重点。第二卷以农业的开展为中心,农业与环境的关系亦贯穿其中。第三卷以古代城市的兴起为主要内容,不少作者也注意到了城市与地形之间的关系。第四卷描述国家、帝国的兴起,环境的内容相对少了一些,但第五卷讨论帝国、文明之间的扩张,环境的因素再度成为一个重要观察视角。第六、七卷以近代以来世界的形成和演变为中心,其与环境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一句话,全球史的写作与环境史研究的开展已经形成一种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关系,其中原因在于两者都突破了国别史的框架。
环境史和全球史关系如此紧密,近年也有不少学者结合两者写作了一些全球环境史的著作。安东尼·培纳 (Anthony Penna) 的《人类的足迹:全球环境史》(The Human Footprint: A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就是一例。培纳在书中开宗明义,指出全球史和环境史的兴起,在两个方面颠覆了近代以来的史学传统,一是走出西方中心论,二是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其他类似的作品还有罗伯特·马克斯 (Robert B. Marks)的《近代世界的起源:15至21世纪的全球环境史》(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nvironmental Narrativ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该作者还写过《中国环境史》(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在环境史领域著述甚丰。在全球史的教科书中,也出现了从环境的视角勾勒人类历史演化的尝试,如罗伯特·布利艾特 (Robert Bulliet)、柯娇燕 (Pamela Crossley)、丹尼尔·赫德里克 (Daniel Headrick)、斯蒂芬·荷西 (Steven Hirsh)、莱曼·约翰森 (Lyman Johnson) 一起编写了多卷本的《地球与它的人类:一部全球史》(The Earth and Its Peoples: A Global History),自1997年出版以后不断再版。布利艾特是中东史专家,柯娇燕专长中国史,赫德里克是科技史专家,而荷西专攻古典世界,约翰森则专治拉美史。这种多方专家通力合作的现象,在世界史、全球史教科书的写作中比较普遍。更有必要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几位作者除了荷西之外,都不是以研究欧美历史出身,而荷西也不是欧美近代史的专家。如上所述,全球史的著述淡化了近代西方的历史意义,此书作者的组合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
显而易见,通力合作是写作全球史的一个办法,但也有像安东尼·培纳那样的学者,以一人之力写作全球的,甚至宇宙的通史,还有大卫·克里斯蒂安 (David Christian)、弗雷德·斯皮尔 (Fred Spier) 和辛西娅·布朗 (Cynthia S. Brown) 等人。“大历史”一词,由克里斯蒂安提出。他于2004年出版了《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一书,用600页的篇幅勾勒了自宇宙生成以来的历史,其视角之博大,叙述之宏富,让读者印象深刻。此书由威廉·麦克尼尔作序,是当代全球史著述中颇有特色的一本。此书的写作,吸收了上述全球史论著的成果,如强调人类之间的网络联系、欧亚大陆环境的“生物圈” (biosphere) 优势等等,而它尤其突出之处是宏观的立场和将人类史与自然史综合考察的取径。克里斯蒂安指出,人类的起源和早期人类的历史形成的是多个世界。而通过人类团体之间的不断互动、交流,网络联系逐渐加强,因此多个世界变成几个世界,最终在近现代形成了一个世界。
大卫·克里斯蒂安的观点,显然是一家之言,其新颖之处是他从人与宇宙的关系来指出人类历史的这一走向。更有意思的是,他在书的最后一章还尝试预测“多种未来”,即近期的未来(100年左右)、中期的未来(1000年上下)和远期的未来(太阳系、银河系和整个宇宙的演变)。弗雷德·斯皮尔和辛西娅·布朗的著作,也有类似的架构——前者著有《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后者写有《大历史:从宇宙大爆炸到当代》(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Present )。他们这种宏观解释人类历史的企图,显现出当代全球史的突出特点,也体现了历史观念的转向。我们可以如此概括,启蒙时代以来的历史观,以普遍性为特征,但这一普遍性其实是西方模式的扩大。因此自20世纪以来,不断有人对之提出质疑。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讨论更挑战了近代史学赖以为基础的“宏大叙事”,使之土崩瓦解、无复重建。新文化史、历史记忆和情感史等学派的兴起,都从各个方面证明了近代史学的终结。但全球史和环境史的兴起则似乎又代表了一个新的趋向,那就是试图在新的基础上重写“大写历史”,对人类历史的总体走向再度提出宏观的看法和解释。这些宏观历史的尝试,必须突破近代史学建立的规则,如仅仅采用原始的史料等,因为史家显然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文字和语言,更无法穷尽所有相关的史料。于是,当代史学似乎又回到了希罗多德、圣奥古斯丁的时代。不过,这显然不是古代的再现,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因为当代史家治史的手段已经今非昔比了。而究其本质而言,史学是人类记忆的延伸和记录,这些记录的目的是总结过去、解释现在和展望未来。古代是如此,今天亦是如此。
台大人气教授欧丽娟,网上金牌公开课“红楼梦”,这才是打开红楼梦的正确方式。


